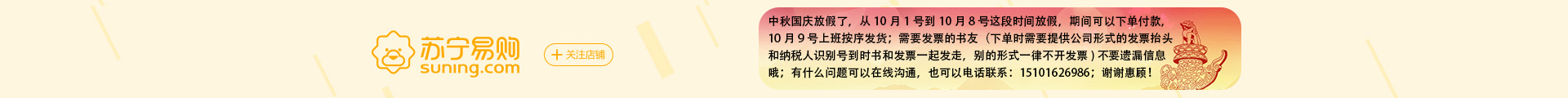由于此商品库存有限,请在下单后15分钟之内支付完成,手慢无哦!
100%刮中券,最高50元无敌券,券有效期7天
活动自2017年6月2日上线,敬请关注云钻刮券活动规则更新。
如活动受政府机关指令需要停止举办的,或活动遭受严重网络攻击需暂停举办的,或者系统故障导致的其它意外问题,苏宁无需为此承担赔偿或者进行补偿。
正版新书]愿你活得通透又自由kiki拉雅9787559424167
¥ ×1
Part 1 我的久别重逢,你的乍见之欢
国境之南的孤岛
哑女与火车
太极镇
从前日色慢
尼泊尔的星空都坠落
Part 2 遇见你的那个瞬间比爱永恒
恩师
化作海豚来爱你
九尾猫传说
晚一点遇见你
Part 3 愿我如初,而你常在
唐人街的假行僧
隐秘的秘密
西贡没有情人
催眠
大理想国的嬉皮士
kiki拉雅,一个像矛盾一样分明的女子,一个爱笑的sunshinelady。她的呆萌可以名列影响你人生的十大表情之一,而她的睿智又属于平行时空里才可以见到的成熟。
拉雅的文字很细腻,总能像水一样潺潺流进你心底,而每一篇文章,都比花解语,比玉生香。总之,她拥有把你从困厄的黑白里拉回来的力量。
爱似风云,无形无相,无定无常。温暖、悲伤、幸福、寂寞,多少面具的背后,是否都藏了一张叫作曾经的脸?爱的睫毛,要被现实夹磨多少,才会有撑起明眸的弯弧?拉雅会告诉你。
/第一位访客/这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一头乌黑的长发,还是少女般的模样。她是在风和日丽的清晨上岛的,老人还记得那天她的长发在海风中飘荡的画面,很美,像一朵正在盛开的花。
老人那时正在小木屋外取水,他看见她的一瞬间,心跳快了一下,他为这突如其来的心动感到羞愧,毕竟他已经这么老了啊,应该是老到无关风月的年龄才对呀。
老人将小姑娘请进屋,她不带一丝笑容,直接坐在了那把椅子上,老人坐在床边点了一支烟斗,两个人的动作都一气呵成,仿佛早已约定过一般。
“我是1938年的那个夏天开始恨他的。”年轻的姑娘说。
我是1938年那个夏天开始恨他的。6月,夏天的热仍在继续,知了的叫声聒噪得很,每年都会如约到来的雨水却迟迟未落,田里干燥得裂出了缝。一切仿佛都在预示,这将是一个不会太平的夏季。
那天晚上我杀了一只鸡,混着蘑菇和玉米炖在灶上的锅里,那味道可香了,我在等我的母亲从镇上回来,那天是她的生日。油灯烧了一大半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急促的敲锣声,村里负责传讯的王大爷在外面喊着:“各家父老乡亲都到戏台集合,皇军有事要问。”我打开门问王大爷发生了什么事。王大爷皱着眉头无奈地说:“不知道呀,村里来了好多日本人,说是要来抓一个共产党要员的。我们村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都是老实安分的农民,哪有什么共产党呀。”王大爷说完叹了口气,又继续敲锣喊起来。
日本人来了,我们是没法躲了,只能去戏台集合。从家到戏台的路并不远,我却像是走了一世那么长,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样的遭遇,让我害怕的是“皇军”这两个字。我们老百姓不懂战争,但也知道日本侵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共产党是抗日卫国的主力军,当然也是那些皇军大肆逮捕的对象。镇上裁缝店里李狗娃的结局全村人都知道,被日本人抓走一个星期后,尸体就挂在了镇里的大牌坊上,血淋淋的,难以想象遭受了多少折磨。
我到戏台的时候,看见戏台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乡亲们整齐地排成队蹲在地上,穿着神气军服的日本军官扛着刺刀在人群前面来回踱着步子,整个气氛压抑到让人窒息。我蹲在人群的最后面,两腿吓得发抖。
王大爷挂着锣鼓小心翼翼地走到军官面前,告诉他人已经挨家挨户通知完了。踱着步子的军官点点头,然后对着人群大声说了几句日语。
旁边戴着眼镜的书生开始翻译:“你们这个村有一位共产党要员,女的,知道的人给我指出来,不然你们都得死。”乡亲们小声地议论着,大家都是一脸惶恐与茫然。等了一会儿,军官开始不耐烦了,拿着刺刀从第一排的人看过去,用蹩脚的中文随便问了一个农妇:“是你吗?”农妇紧张得连连摆手:“不,不是我……”但还没说完,大家就听见了农妇的惨叫声,只见刺刀从她的肚子穿过又拔出。农妇倒在了地上,鲜血开始在这片黄土地上蔓延,所有人都处在极度恐慌的状态之中。
“你们快说吧,别包庇了,他们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啊。”戴眼镜的书生着急地说。
此刻,人群里站起一个少年。这个少年长着我熟悉的脸,那张黝黑的属于黄土地的脸,那张对我笑时露出洁白牙齿的脸,此刻,他结巴地对军官说:“我……我……我知道是谁。”他就是这样,以前在学校里上课时也是,每每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就紧张,一紧张就结巴。
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是……是画眉她娘。”他话音刚落,全场哗然。
“你放屁!你为什么要冤枉我娘?”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和他像两个在高堂之上接受审判的犯人一般,已经没了尊严可言。
戴眼镜的书生上前问他:“你确定?”“我看见了,就在镇上,看见画眉她娘和一个共产党交头接耳。”他说。
“你放屁!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两个日本人过来将我押住。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放了乡亲们,和他们无关。”身后传来我娘的声音。她背着才从镇上收摊回来的背篓,挺直了腰杆站在人们面前。我娘是嫁到这个村里来的,我爹死得早,我娘为了把我养大,去镇上卖东西赚钱,村里谁家有困难找我娘借钱,我娘都会伸出援手。大家都知道我娘是个老好人,却从来不知道她是个共产党,还是个要员,连我这个女儿也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
日本人围向我娘,她被他们紧紧押住。那个日本军官走了过来,用手抬起我娘的下巴,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日语。我娘向他吐口水,他狠狠地回了我娘一个耳光。我看见我娘的嘴角流出血来,她直直地望着那个军官,眼神里像藏着刀,我从没见过她这个样子。那一刻,仿佛周遭都安静了。
我和我娘在监狱里那会儿,他们每天都来提审我娘,每次都被打得伤痕累累。最后一次,她回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但她强撑着身子起来,往监狱的地上洒了一碗水。她说这是最后一次敬我爹了,过不了多久就能见到他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只是哭,她替我擦了擦眼泪:“画眉啊,娘下辈子再给你做酸梅汤喝。”“你娘的酸梅汤做得真好喝。”年少的他总和我说这句话。
“那我以后天天带给你喝好不好?”“你真好,画眉。等我长大赚了钱,我一定要娶你做媳妇儿。”“真不害臊,谁要做你媳妇儿。”“你啊,画眉做我媳妇儿,画眉做我媳妇儿,哈哈哈。”我和他倒在草地上,风拂过树梢,知了在欢唱,我们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要是时间就停留在那个夏天该多好。我就不会失去我娘,也不会失去对长大的向往。
/第二位访客/这是一位中年妇人,她穿着碎花长裙,裹着一条开司米羊绒披肩。她上岛的时候,老人正在准备午餐。老人把妇人请进屋,给她倒了一杯水:“待会儿你正好可以留下来吃个午饭。”妇人点头答应着,便坐到了椅子上。
“我的丈夫是位中学老师。他却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妇人停了下来,温柔地等待着老人的反应。可是老人没有回应她,只是默默地抽着烟,眉头皱着,仿佛烟不好抽,又仿佛妇人的话引发了老人的沉思。
我的丈夫叫李军国,我和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是中学老师,我是纺织厂的女工,都是有稳定工作的人,觉得对方各方面还过得去,也没怎么谈恋爱就结婚了。但是我自知是配不上我丈夫的。他是个文化人,我只是小学毕业,勉强能认得几个字。我们那个年代,没多少人是真的自由恋爱过来的,情啊爱啊,在那个年代说出来都怕人笑话。可是呀,能白头偕老的夫妻,却多是那个年代的人。你说奇怪不。但我知道,我对我丈夫是喜欢的,从我见到他的第一眼起便喜欢。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支派克牌的钢笔作为聘礼,花了他两个多月的工资呢。我们搬进了学校分配给他的房子。房子虽小,也够我们夫妻俩生活了。后来,国家提高了教师薪资待遇,我们的日子就更加顺畅起来。有了孩子以后,我们便在学校附近用两个人的积蓄买了一套房子。陪着丈夫,把孩子带大,是我当时最幸福的目标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抽屉里发现了丈夫和一个女老师的通信。那女老师来过我们家里。她长得很乖巧,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才从师范大学毕业,去他们学校实习。她时常和他一坐就是一下午,他们有时候会争执几句,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跟她讲。我在厨房里烧着水,他们的茶要是凉了,我就去给续上。我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聊什么,但是看着丈夫神采飞扬的样子,我感到满足。
从信里看,他们的关系已经持续一年了。他们聊诗歌,聊政治,聊一些他从不会跟我聊起的话题,也说一些缠绵的密语,他还在信里给她取了一个可人的昵称。说实话,我看到那些信件,那些丈夫情感游离的证据之时,我并不恨那个女老师,而是嫉妒她,非常嫉妒。我从来不知道平日里一板一眼、严肃正经的丈夫,也会有如此温情的一面。
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很幸福,我们的工作顺利,还有一双懂事的儿女。可是我也忽略了,我的家庭除了柴米油盐,好像确实也没有别的事物能让我和丈夫都心生热情。
他们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女老师转到别的学校任职以后才渐渐淡了下来。直到儿女长大成人,我也始终对此事守口如瓶,从未向丈夫提及。你若问我为什么这么能忍,我想这不就是日子吗?没有人是一生都不会犯错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以前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东西坏了就拿去修,能修好就不会丢掉。可现在的人啊,东西还没坏,就想着要换了。
/第三位访客/这个男人上岛的时候,落日失去了它最后一点光亮,掉入了海中,大海便沉浸在了黑夜的呼啸里。海浪拍打着海岸、礁石,归巢的海鸥轻抚过海面,留下绵长的余音。看样子,今夜该是要下一场大雨了。
到访的男人有备而来似的穿着黑色的雨衣,雨衣的帽子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老人在屋里点好了灯,静静地等待访客进来。男人没有敲门,径直开门走向了床边。
“你来了。”老人说。
“是的。”男人的声音略显苍老,他背对着油灯坐着,脸依然隐藏在帽子的阴影里。
“她已经死了。”男人说。
老人拿烟斗的手打了一个颤,烟灰掉落在了干净的地板上。
“她早就死了。”男人继续说,他的声音带着哭腔。
是我欠她的,这一辈子都欠她,可是我没有机会将这债还了。她被白布裹着抬出来的时候,我连看她的勇气都没有。她和她娘被村民埋到后山的山头之后,我只去过一次,也只敢远远地看一眼她的坟头。那哪里是坟啊,连个墓碑都没有,就是一个乱土堆,长满了杂草。我就那样看着,忽然看见一只金黄色眉鸟停在了坟头上。那只画眉长得真好看,羽毛在阳光下泛着光。它就直直地看着我,那眼睛炯炯有神,像是藏着刀,我不敢和它对视,它盯得我心发慌,我赶紧下了山。
“画眉她娘并不会怪你。”老人说。
“可是我怪我自己。”男人说。
“你也是不得已。”老人的语气里充满了沧桑和无奈。
“可是画眉死了。”男人把头压得很低很低。
“你觉得你对不起画眉。”“我觉得我对不起画眉。”“你也对不起你妻子。”“我也对不起我妻子。”“你为什么要对那个女老师动情?”“因……因为她长得太像画眉了。”男人哭了起来,他的脸在他抽搐的哭泣里渐渐浮现出来,那是一张和老人一模一样的脸。
老人摁灭了烟斗:“你走吧!”此时外面已经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风把木屋吹得嘎吱响,大海在暴风雨里发出如猛兽一般的咆哮声。男人起身整理了下雨衣,打开门,朝黑暗的大海里走去了……/尾声/“国境之南有一座无名的小岛。小岛很小,小到只够一群吉卜赛人围着火堆起舞。然而这里从来没有过这么热闹的场景,这是一座只属于一个人的孤岛。”“李大爷又在讲故事啦?”护士小姐推着装满药罐的小车进来,在老人的单人病床边放了一瓶药。
“奶奶,您对大爷可真好,这故事您都听了百八十回了吧,还听不腻。”护士小姐打趣道。
“孩子们都出国了,只有我在这里能陪陪他。他想说就让他说吧。”病床边的椅子上,一位披着开司米羊绒披肩的老妇人一脸温柔地说道。
她的手里捧着一个盒子,盒子里有一支派克牌的钢笔和满满的信。信已经有些年头了,信封上的寄件人写着:小画眉。
“画眉已经很久没有给我写信了。”病床上的老人说。
“在呢,在呢,你看画眉给你写了那么多信呢。”老妇人笑眯眯地回复道,那模样像是在哄一个小孩。
老人转头握着老妇人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画眉,对不起。”老妇人的眼睛湿润了。她望向窗外,窗外不远处有一片海滩。而他们正身处海滩边上的一栋白色建筑里,建筑里老人的房间门上贴着一个病历牌:李军国,70岁,老年性痴呆症,病程十一年。
《哑女与火车》引言:这个城市对周生来讲已淡化成了一杯白开水,没有滋味却不可缺失。
/1/周生十八岁那年退学了,一个人在镇上的火车站做点小生意。说是做生意,其实是在站台上,趁着过往的列车停站那几分钟,为车上的乘客提供些零食、水,或者用以打发时间的报刊。这样平淡无奇的日子足以麻痹一个热血青年,周生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点一点磨去了昔日的棱角,慢慢地习惯了车站的油烟味、嘈杂声和每天上演的各种悲欢离合、聚散苦多。这个城市对周生来讲已淡化成了一杯白开水,没有滋味却不可缺失。周生偶尔还是会幻想,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会发生些什么,是的,故事里总是这样写的,周生也觉得自己十八年的时光里应该发生点什么。可是,要如何去期待在这样陌路人来去匆匆的车站里会有荡气回肠的故事呢?
/2/往返于湾镇和代城之间的绿皮火车上总是坐着一个女孩。她随意地扎着一束马尾,穿着浅灰色的针织衫。周生注意到她不像其他乘客那样会在列车停站的空当探出头来到处张望,或买点东西,或靠在窗口吸上一根烟,或与其他认识不认识的人高谈阔论。女孩很安静,她最多也就把头靠在窗棂上发会儿呆。这是周生第一次看见湾湾,彼时,她是不知去向哪里的旅人,而他却是固守此地的小商贩。周生想上前打个招呼,可是又怕太突兀,火车在周生犹豫不决的时候又启程了。
她是去代城吗,还是就在下一站下车?其实不论是代城还是下一站,周生都没去过,他打一出生就没有离开过他所在的小镇。周生逼迫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因为他很可能不会再见到这个女孩了,她只是个过客,于是周生又卖力地吆喝起买卖来。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在从代城返回的城际列车里见到了那个女孩,仍然是坐在一个对着他摊位的靠窗的位置。她也看见了周生,对他笑了笑。这一次,周生没有再犹豫不决,在这个世界能碰见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他和她还是第二次遇见,这一定是缘了。
于是他鼓足勇气径直走向女孩,很小心地问了句:“要看报吗?周刊、晨报、晚报都有。”周生觉得这个搭讪的借口简直是烂透了,不过他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
女孩抬起头来,眨巴着大大的眼睛说:“好呀,有什么报纸?”“周城晨报,湾镇晚报,代城日报都有的。”周生利索地介绍起来。
“给我一份周城晚报吧。”女孩说,周生刚把报纸递过去,列车就鸣笛了,女孩着急地说道,“我还没给你钱呢!”“我叫周生!”周生急忙报了自己的名字,至于报纸钱,压根就被他抛在了脑后。
“湾湾!”女孩对周生挥了挥手,然后列车开走了……周生发现,湾湾每周都会乘坐这辆火车,而且总是坐在离周生摊位不远的窗口位置。对于周生来说,湾湾是本让人猜不透的书。她来来往往的旅途里,似乎就有无数的故事在里面。周生唯一知道的就是湾湾去的是代城,她在代城上大学。有时候,周生会看见湾湾提着一大篮水果或其他吃的去代城,回来的时候篮子空了,湾湾却洋溢着满脸的幸福。有时湾湾返程的时候也会带些新的东西,偶尔会给周生带点小礼物。
周生看过一部电影叫《周渔的火车》,他甚至怀疑湾湾就是另一个周渔,而火车的那边就住着一个陈青,这样的想法让他受尽折磨,备受折磨的同时,周生意识到一个事实,他喜欢上湾湾了,这个每个月都可以见上几面的湾湾,虽然每一次见面都只有那么几分钟,但周生已经很知足了。
他会在火车到站前就想好要对湾湾说的话,有时候他们会聊聊天气,有时候湾湾会跟他讲讲代城的繁华,城里又修建了多少层的高楼,姑娘们都穿着怎样流行的衣饰。周生也跟湾湾讲周城的事,而在周城这个小镇里,周生最熟悉的就是这个站台。
周生跟湾湾讲过一个故事。大概是在二十多年前,这辆火车在经过周城通往湾镇的路途上差点发生事故。那个年代的火车站台比现在开放多了,周城是个小站,却连接着湾镇和代城,成为了两个城市之间的枢纽。因为火车是一个星期才往返一班,所以每周火车出动的时候,这个小站就成了热闹的集市。从代城运过来的洋气的头绳、玩具,从湾镇运过来的新鲜的蔬菜、水果,都会集中在站台这一处小小的地方售卖。
那天下着大雨,快到中午的时候,站台来了一个背着背篓的哑女。她是从湾镇过来的,扎着两根长长的大辫子,背着一背篓的菜,到了站台却不卖菜,而是急匆匆地朝站台控制室的方向跑。她一面比画着,一面用喉咙发出呜呜的声音,那声音显得十分焦灼,她好像想告诉工作人员出了什么大事,却又说不出话来。值班的工作人员以为她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残疾人,草草地要打发她走。她被赶出来的时候都快急哭了,情急之下,只见她抓起身边一个农夫手里的鸡就往雨里跑去。鸡刚被农夫切断了脖子正在放血,鸡血在站台上流成了河,她边跑边脱下自己穿的棉麻薄衫,把鸡血往薄衫上抹。所有人都站起来望向她,谁都拦不住她,她就像疯了一般不断地往前跑,直到消失不见。
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笛声,从代城开过来的火车进站了。一拨又一拨的人下了车,然后一拨又一拨的人上了车,看热闹的人群也立马回到自己的摊位上,在这个人来人往的交错之际,商贩们抓紧时间吆喝着自己的生意,谁也不在乎那个疯哑女怎么了,更不在乎她究竟要去向哪里。
“她去了哪里?”湾湾问。
“你下周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周生说。
/3/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驾驶着从周城驶向湾镇的那列火车的司机,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所见到的那一幕。在通向湾镇的大桥上,他看见雨雾中,列车行驶的正前方有个满身是血的女人挥动着一块鲜红的布。他鸣笛,使劲地鸣笛,企图让那女人赶紧离开轨道,可他越是鸣笛,女人越是挥动手中的红布。司机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强行刹了车,列车停在了距离女人不到一米之处。
司机打开驾驶门下车,正准备开骂,可话刚到喉头就咽了回去,一股冷汗从脊梁骨上冒出来。他看见就在列车前方一米开外的地方,桥断了。如果不是眼前这个疯女人,整列火车的人恐怕都得命丧于这滔滔江水之下。可是如果那列火车没有停下来,或者没有刹住车,这个女人也得牺牲掉自己的性命。
从那之后,哑女成了英雄,政府为她颁发了锦旗表彰她,还给她发了奖励金,周城甚至一度掀起了“学习哑女精神”的活动。但是周城里却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也没有人问过她的名字,大家都习惯叫她哑女。然而这股热潮很快就过去了,日子平淡下来后,哑女依然是平静地种田卖菜。据湾镇的人说她是一个弃儿,村里书记可怜她,就给她分了点土地。二十多岁的哑女还没有嫁人,因为没人愿意娶个哑巴回家。后来村里有一年大丰收,雇了一群外乡人帮着收割庄稼。那些外乡人一待就是大半年。其中一个青年喜欢上了哑女。
没过多久,哑女未婚先孕怀了青年的孩子。但青年最终还是离开了,农忙之后就去别处务工了。据说,哑女怀着孩子追着火车走了很长的路,青年就这样留下了她和孩子。人们都以为她可能经受不住这个打击,会疯掉,然而没有,哑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活得更努力。虽然她被人抛弃了,但她不怨;虽然村里人对她各种白眼,明目张胆地议论她不守妇道,但她不在意。她从小孤苦伶仃一个人,而今变成两个人了,她的日子有了最重要的意义。
“你见过哑女吗?”湾湾问。
“没有,我妈说火车站里的站台规范整治以后,站台集市没了,也就再没有见到过哑女。”周生说,“对了,湾湾,你在湾镇应该听说过哑女吧?”“嗯,听我妈说过一些。”湾湾笑呵呵地说。
火车又一次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不一会儿就开走了。
周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持续多久,毕竟湾湾始终都是作为一个过客的角色出现在他的世界里。他想要留住她,哪怕她能下车留在小镇片刻也好。他可以带她去小镇逛逛,请她吃他最爱的小吃,还可以去他家屋前的浅水滩踩水。可是周生的邀请总是被湾湾婉言拒绝了,这让周生更加确信代城里有“陈青”的存在。但是周生没有办法,只能和每个月的那几分钟的停车时间赛跑,就这样,周生不知不觉已经跑了快要一年,但他还是在原地,而湾湾也始终坐在靠窗的位置。
/4/年底最后一个月里,周生看见湾湾趴在列车窗口怅然若失的样子,她也没有对周生打招呼。周生暗喜,她是不是要离开那边的“陈青”了?可是他转念一想,自己不是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了吗?心里便不由得生出一股失落。周生怕,真的怕。
“湾湾,你能下车来吗?就片刻也好。”他终于鼓足了勇气。
这次湾湾没有一下子就回绝,眼睛里充满了惶恐和犹疑,她直直地望着周生,仿佛他的眼神里有她想要确定的某个答案,然后她点了点头。周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脑袋里开始浮现出和湾湾一起奔跑玩耍的画面。可是当湾湾从车厢走下来时,他呆住了,所有的期待都在那一瞬间戛然而止。
湾湾拄着拐杖,一晃一晃地走向他时,看见了周生诧异的目光,这目光直逼进她的心坎,像无数的针扎进她的心脏,血淋淋的。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湾湾把声音压得很低。
周生一时说不出话来,低着头不敢看湾湾,手心竟捏出汗来。沉默让时间凝固了,湾湾知道在如此尴尬的见面里,她一定显得多余又可笑,她看了看周生,然后默默地转身向列车门口走去。
周生想要叫住她时,湾湾突然回了头:“周生,那个哑女叫张翠花,她是有名字的。”说完便不给周生任何开口的机会,就准备上车。
湾湾的拐杖不小心卡在了火车的铁踏板上,周生想过去帮她,还没到湾湾身旁,就看见另一个男孩帮忙取出了拐杖,扶着湾湾上了车。
这时火车开动了,周生傻傻地立在站台,像一尊雕像,看着车子渐行渐远。见惯了离别的他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他知道他很可能至此永失了湾湾。
/5/湾镇一座小小的砖瓦房里,湾湾走进厨房,一个满脸皱纹的妇人正在灶台前收拾,湾湾拍了拍她的肩,打着手语问:“妈,能跟我说说爸爸的事情吗?”妇人一愣,将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拉着湾湾在客厅坐下,打着手语回道:“你是不是一直以为爸爸抛弃了我们?”见湾湾点点头,妇人继续用手语回道,“不是的,他没有抛弃我们,是我骗了他。”二十几年前的社会,虽然已经不是那个女子不清白就要被浸猪笼的旧时代,但对于湾镇这个闭塞的小地方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件丢人的大事了。当哑女未婚先孕的事情被传开后,村里的妇人都对此义愤填膺。她们觉得哑女丢了村里的脸,她们组队拿着锅碗瓢盆,正义凛然地赶到哑女的屋里,要把青年赶出村去,她们还撕碎了哑女的锦旗。
“不守妇道的妇人根本不配得到这面锦旗。”她们一面撕一面骂着。
青年被赶出村子躲到了镇上。离开的前一夜,青年偷偷去找哑女,让哑女跟他走。哑女不肯走,她从小就在这个村里生活,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而且她离开又能去哪儿呢?
更何况,青年和其他的务工人员是不一样的,他攒够了钱是要去城里念书的,他有一腔的抱负,他的家人肯定也是容不下她的。她既然不能跟他走,那就不能耽误他。于是哑女对青年撒了谎,撒了个天大的谎,她告诉青年,她已经把孩子拿掉了。
“爸爸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湾湾惊讶地道。
哑女点点头:“他很生气,生我的气,此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你可以不用这样的。”湾湾比画着手语。
“这是我的命,我认了。但至少还有你,我就觉得这辈子也够了。”哑女打着手语,眼角已经泛红。
湾湾帮她捋了捋头发:“妈,我不坐火车去代城了,从今以后我改坐汽车了。”“你不想去见那个少年了吗?”“不见了。”湾湾低头看了看自己残疾的腿。
“是妈对不起你。”哑女哭着比画,“你三岁那年在院子里被榔头砸到了腿,要是我能听得见你的哭声,早点把你送进医院,说不定你的腿也不会这样。”“妈,”湾湾打断了母亲的话,“你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已经很厉害了。放心吧,我会遇到像我爸那样不嫌弃我们的人。”说完,湾湾便拿起已经收拾好的行李准备去车站。母亲一直送她到屋外,湾湾回过头,看见母亲身后那面被黏合好的红色锦旗,上面写着:英雄张翠花。
妈,你就是英雄,我的英雄。湾湾对着母亲挥了挥手。
亲,大宗购物请点击企业用户渠道>小苏的服务会更贴心!
亲,很抱歉,您购买的宝贝销售异常火爆让小苏措手不及,请稍后再试~
非常抱歉,您前期未参加预订活动,
无法支付尾款哦!
抱歉,您暂无任性付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