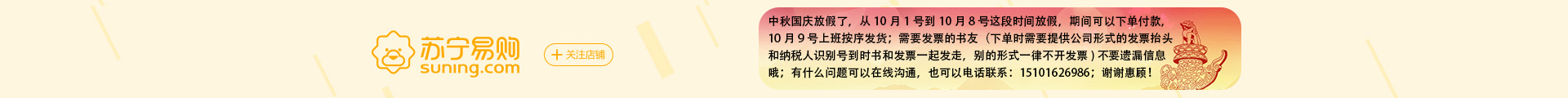由于此商品库存有限,请在下单后15分钟之内支付完成,手慢无哦!
100%刮中券,最高50元无敌券,券有效期7天
活动自2017年6月2日上线,敬请关注云钻刮券活动规则更新。
如活动受政府机关指令需要停止举办的,或活动遭受严重网络攻击需暂停举办的,或者系统故障导致的其它意外问题,苏宁无需为此承担赔偿或者进行补偿。
正版新书]悟能马德华9787570207947
¥ ×1
第一章
我生之初尚无为 / 001
第二章
命中注定戏中缘 / 013
第三章
取经之路多坎坷 / 049
第四章
大智若愚品八戒 / 115
第五章
良师益友伴我行 / 131
第六章
艺海无涯修远兮 / 169
第七章
修身齐家古稀年 / 207
朋友眼中的马德华 / 234
险成舞蹈演员当人们讲到勤奋时,总爱说个词儿,叫闻鸡起舞。练武术的人更不例外,每天天还没亮,随着一声鸡鸣,父亲便拎着我起床练武了。我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敢拒绝,只得乖乖地去练武。
父亲把我叫醒之后,便到厨房里帮母亲忙活家里早点铺子的营生了。 母亲熟练地转动磨豆浆的磨盘,父亲把和面的盆子磕得叮当响,准备好炸油条、油饼的面团。把面团往烧滚的油锅一扔,只听接连几声“啦”的声响,满屋瞬间全是油酥的香气。等炸油饼、油条、豆浆、杏仁茶全预备好了,还不到五点,家里的早点摊子也就准备营业了。
我的生活每天基本都是如此,从四点半练到六点半,两个钟头后才能吃上早点,紧接着就要去上学。我练武的地点在家门口的一个宽绰的地方,从打拳、踢腿,再到刀、棍、枪、护手双钩,兵器拳脚一样都不能落下。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到我们家来吃早点,一是冲着父亲信奉的“真 材实料”这个生意经,另外一点则是喜欢来看我练武。其中的道理有点像天桥撂地艺人惯使的“圆黏儿”(就是用一些特殊手段招揽观众的意思),大家可能觉得这是我们家的一个特点,一边吃着早点,一边还能看我练武术,时不时地还能叫个好。可我只能饿着肚子,看着他们嚼着 金黄的油条,就上一口豆浆,心里这个馋劲儿就别提了。
我刚开始练武的时候最恨家里那只鸡,心里想着早晚把你炖了吃肉。 可练的时间一长,身体慢慢强健起来后,倒也不觉得怎么苦了。再加上每天都有满座的“观众”给我叫好,从此清晨的练武不再只有不情不愿和满腹委屈了,成了我一天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当时的空政文工团在灯市口同福夹道里面,离我家不远。有一位那里的干事,经常穿一件四个兜的军装。
那个时候区分战士和干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看衣服,战士两个兜,干事四个兜。他每天必来我家吃早点,一个油饼,一碗豆浆。没几天我便记住他了,总叫他“四个兜”叔叔。
他大概是喜欢我这个年轻气盛的孩子,也觉着我是个学舞的好苗子。 有一天我练完武术,正吃着早点,他走到我的身旁。
“小子,你愿不愿意当兵参军,也穿上四个兜?”他微笑着问我。 我心里乐极了,那个时候,我看见有的娃娃兵穿上军装,特别英武,打心眼里就羡慕!于是连忙点头说:“怎么不愿意?”“我们那儿正在招收一批小学员,你愿不愿意去试试?”我心里甭提多开心了,要是上戏曲学校,父亲肯定不让我去,但如 果我去当兵,父亲一定会同意的!
“太好了!那我跟你去!”“那就走嘞,跟我上文工团那儿去!”四个兜叔叔和我父母打了声招呼,便带着我走了。 这一路上,我特别兴奋,一直缠着叔叔问东问西的,就在这时,路边人家里忽然传来一阵京戏声,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叔叔,我去你们那儿能唱戏吗?”我问道。
“唱戏?我们又不是剧团,我们这是文工团,主要是招舞蹈演员。 我看你武术练得不错,动作非常协调,悟性也可以,教你一些动作,你很快就能学会,是个好苗子,来我们这儿学舞蹈应该挺好的。”我脑子一蒙:“您稍等会儿,您那儿是干什么?舞蹈?跳舞?那我就不去了。男的跳舞,多寒碜呐。”他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你就想唱戏?”我郑重地点点头:“对,没有唱戏的,我就不去了。”“我们这儿没有京戏,学戏曲得到正式的剧团,像北京京剧团、中国京剧院这一类的才行。”“中国京剧院……中国京剧院……”我小声嘟囔着,从那以后,这个名字便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险成话剧演员空政文工团的事情作罢后,我又错过一次机会。
我有个舅舅,参加过抗美援朝,1958年回国。自打他回来那天起,连着好一段日子,我的家里都是“客满为患”,前来看望他的左邻右舍都说他是个战斗英雄,是“最可爱的人”。
我舅舅在抗美援朝的时候立过战功。他是个铁道兵,搞运输、架桥之类的工作。战争胜利后,介绍他们事迹的剧作和文章有很多,都在歌颂他们创造了生命线。
那个时候的小孩,对解放军有一种无限的崇拜,我也不例外,逢人就说我舅舅是战斗英雄。舅舅也很喜欢我这个小外甥,经常带着我去铁 路文工团看演出。有一次,我在文工团里玩的时候,忽然一阵胡琴的声音吸引了我。什么?这个文工团里有唱戏的啊?我在院子里听了好一阵子,心里笃定一个想法:我要来铁路文工团学戏。
晚饭的时候,我试探地问我舅舅:“舅,你们那儿的文工团招学员吗?”“招啊,现在好几个文工团都在招人。”舅舅回答道。
我一听,这事有门,又问道:“那你们文工团,也全是唱歌和跳舞的吧?”“除了唱歌和跳舞还有话剧,可以到那儿去当演员。小子,我看你平常好动,你可以去试试。去文工团可是个好差事。”舅舅和我说。
“我中午在您那儿,听到还有唱京剧的啊。您看看我能不能去学戏啊?”我想着去文工团父亲肯定是支持
的,要是还能唱京剧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早知道你会提京剧。”舅舅看了看我,“京剧团是他们铁道兵里头的一个业余的剧团,都是一些退下来的老战士,他们搞了一个特别的工会,一块弄的一个业余的团。”我高兴地说:“业余的也成!”舅舅急得一拍桌子:“业余的哪成?你这么点儿孩子,每天和老兵们混在一起,太不像话了!”我吓得一缩肩膀,没敢再说话了。
舅舅瞪了我一眼,说道:“德华啊,你听舅舅一句劝,还是上铁路文工团,那儿真挺好的。你想想,咱们铁路的文工团,将来能坐着火车去全国各地,你想到哪儿去演出,就到哪儿演出,多威风啊。”我一拨楞脑袋:“您这儿没京戏,我不去。”“嘿,你这小子,那话剧呢?”我撇撇嘴,说:“话剧我也不去,站在台上的人没有锣鼓衬着,也 没有胡琴,像个傻大个儿往那儿一戳,光在那儿说话,不好!话剧没劲!”舅舅被我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叹了口气。这样,去铁路文工团的事也只得作罢,再没被提起过。
后来等我真的演了戏之后,总能想起来自己曾经稚气未脱的样子。
如果那个时候能在话剧团里有一番锤炼,实在会对表演有很大的一个提高。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使我这么笃定地想考京剧院,这大概就是戏曲舞台的魔力,和孩提时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时,那一份初心和童真吧!
我就是要唱戏我打小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戏迷。
戏迷有个特点,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听见胡琴响就走不动道。不管自己是否天生五音不全,不管别人是否喜欢听戏,逢人必讲某某老板的身段、唱腔多么优美,逢大角儿的戏必到戏园子里一饱耳福,即使手头拮据,也要站在门口听上两句“蹭戏”。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 里都有反映戏迷的作品,戏曲里还专门有出戏叫《戏迷传》,拿戏迷找乐开涮。
但戏曲真的有一种魔力,最吸引我的,还是舞台中央熠熠生辉的大英雄。仿佛唱起“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时,我真的就变成了日审阳、 夜断阴的包拯。正是凭着这点喜爱,我从那时就下定了一个决心—我一
定要学戏!
有一天,我的师哥—也就是我武术老师的儿子—突然对我说:“德华,你知道吗?中国京剧院正在招收学员。要不咱俩试试去?”太好了!我想都没想,一口便答应下来。可转念一想,我该怎么和我父亲说啊?
果不其然,父亲听闻我这个念头立马着急了。父亲本想努力赚钱供我上大学,好让世代农民的家里出一个文化人。解放后,虽然戏曲的地位有了提升,但唱戏仍不算是一件风光的事情,但凡家里有出路,绝不让孩子去学戏。父亲也坚持这样的观点,因此我决定等父亲的心情平静下来再次跟他请求。
我是从来不敢与父亲争执的,见到父亲就像避猫的老鼠一样,只能在父亲面前表现得好一些,希望换得他的同意。但无论我怎么请求,父亲始终是反对的,甚至怕我偷偷地报名,把家中的户口本也藏了起来。 母亲一向溺爱我,我决定从母亲这方面做工作,其实小孩子的把戏无非是撒娇和装委屈。几番软磨硬泡后,母亲终于经不住我的哀求,也 感觉到了我对戏曲的热爱。于是我偷偷和母亲商量后,便拿着自己平时攒下来的两元钱,“偷”出了家里的户口本,和我的师哥一起去报考了中国京剧院学员班。
当时的中国京剧院在北池子,我们俩手拉手一路小跑到京剧院,到了门口我们吃了一惊,横幅下面挤满了来报名的人。后来得知有2000多人报名,学院只准备招收60人。
我自恃有些武术的功底,加之平常又爱看戏、哼戏,果然,经过几轮筛选,我和师哥都成了入选的幸运儿(实际当时京剧院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只招收了54人)。我们俩乐疯了,一路笑着、叫着跑回了家,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终于如愿以偿了,仿佛自己是天下最最快乐的幸运儿。
像是一棵突破了种子的外壳、冲破了黑暗土壤的小草,我看到蓝天、 白云、水滴,感受到风,感受到阳光的温度。这是梦想与热望,还有什 么比它们更有力量?
与父亲约法三章我与父亲的关系很微妙,也最正常不过。
中国的父子很有意思,很少交流,但却无时无刻不流露出相互的爱。 父亲的思想观念是老一套—丈夫立世,文成武就。
我显然和他的期望大相径庭,通过了中国京剧院的考试,一阵狂喜过后,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该怎么和父亲交代啊?
回到家中之后,我好像成了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手里拿着录取通知书,先是找到了母亲,喃喃地说道:“妈,我被录取了。”母亲诧异地接过通知书,仔细辨别了那几行字,抬头看了看我:“你想想怎么和你父亲说吧。”我知道母亲做不了父亲的主,一时也不知所措。
我耍了个小聪明,把通知书放在了桌子上,等着晚上回来看父亲的反应。果不其然,父亲先是什么都没有说,把我叫到跟前,狠狠地扇了我两巴掌,紧接着是暴风骤雨般的斥骂:“小王八蛋,长本事了?”我脸上一阵火辣辣地疼,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却又不敢顶撞父亲,只是小声嘟
囔了一句:“爸,我就是想学戏!”父亲是不理会这些的,面对在他眼中不懂事的我,他唯一的方法就是一个字—打。
我结结实实地挨着父亲的打,但是父亲的训责我却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心中只想着我要学戏。这股子犟脾气,也算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吧。
这一幕把旁边的母亲吓坏了,她急忙上去劝阻父亲。可父亲的脾气上来,母亲是劝不住的,他反质问起母亲:“他哪里来的钱报名?他这样你也不管一管?”母亲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姐姐见到架势不对,不敢上来劝架,急忙跑到隔壁,把教过我武术的王大爷找了过来。王大爷与我父亲交好,一听说父亲在打我,赶忙跑了过来,进门便把我父亲拦下了:“兄弟,有话好好说,打孩子干吗啊?”父亲还是怒气未消,指着我鼻子说:“你自己问问他!”我当时除了哭什么都不知道了,抽抽搭搭地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个大概。王大爷听完之后,对父亲说:“兄弟,孩子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好事,就当是个兴趣爱好培养也是好的啊。”“兴趣爱好?他要是学了戏,就不知道学习了。另外学戏是个小事吗?总讲究个打戏,就这份打,他能挨下来吗?”直到我长大成人,稍有些成就时,父亲才对我说出了当年的苦衷。 过去老人们一说学戏,叫“八年科班胜蹲十年大狱”,每天挨打是家常便饭,身上不规范刀坯子招呼,嘴里不清楚就用烟袋锅子生往嘴里捅。 当时父亲认为我学戏还是老戏班子那一套,谁舍得让自己的儿女受这份罪啊?
好在父亲的态度多少还是有些缓和,对王大爷说:“这孩子做事没有长性,仅凭着一点小聪明,今天高兴想唱戏,等累了、烦了,明儿个又去做其他的事了。将来指着这个吃饭,这样怎么能行啊?”“兄弟,我觉得这个孩子对戏曲有点灵气儿,我带着他出门,只要 有唱戏的,他就走不动道。他既然喜欢这个,就一定能够下心思学!”说完,王大爷冲我使了个眼色。
我止住哭声说:“爸,我一定把戏学好!”父亲叹了口气,对我说:“我可跟你说好了,过去学戏是要签生死文书的,以后你要说你受不了这个苦,回来说不想干了,这个家可不容你。再想上学去,我可不给你花那个学费。今天当着你王大爷的面儿,咱们也来个约法三章。
第一,不管戏班里再苦再难,不许打退堂鼓,要想干这个,就得干到底,咬着牙也得挺过去。
第二,去了学校学戏,尊师重道,要是让我知道你在学校里做了什 么丢人的事,我可不容你。
第三,既然学戏就好好地学,以后混不出名堂来,家里不供你。”我一听,甭说约法三章啊,就是三十章、三百章我也签!
父亲见我这么坚持,最终还是拗不过我,把录取通知书还给了我。 当时我就认定了一个信念—再苦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下去!
就这样,我拿着这张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书,上面饱含着父亲的隐情、母亲的慈爱和我的那份坚持,走进了京剧世界的这扇大门。
苦练基本功
自从进入中国京剧院后,我的艺术生涯才开始走上正途。
其实细想一下,如果当时我真的跟着“四个兜”叔叔,或者跟着我舅舅去了文工团,学了跳舞、话剧,现在也许又是另一种活法。不过,无论我做什么,也应该离不开戏曲。能把自己的爱好作为职业,算是我最
大的幸运吧!
演戏这个行业确实是苦,讲究练二五更的功夫,个中滋味只有同行的人才能体会到。我来到京剧院后,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练功,这个我倒是不怕,每天起床之后,迅速地洗漱完毕,就开始排队练功,有点军事化管理的意思。洗漱完之后不许吃东西,戏谚说得好,叫作:“饱吹饿唱”,师兄弟们一起排队从北池子走到中山公园开始喊嗓子。
戏曲里的喊嗓儿是必修的功课,以前戏台子上没有麦克风,演员必须用一条肉嗓子,保证不管多远的观众都能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说的话。 所以必须通过喊嗓儿练出一条功夫嗓来。
喊嗓儿先是练横竖嗓音,就是“咿”“啊”两个字。“咿”是竖音,往上拔着喊,长调门;“啊”是横音,气沉到丹田,从喉咙里直接发声,为了打远儿。还要喊“呔”“哇呀呀”“叭”,训练喷口、舌根、唇齿音。 等把嗓子差不多喊开之后,再去练习“叫板”,比如武生的“马来”、 老旦的“苦啊”、老生的“走啊”、小花脸的“啊哈”。练完“叫板”,最后练习“打引子”“念白”,体会人物的情感状态。但绝对不会练唱,以防没有胡琴跟着,掉板跑调。
古语云“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做事情贵在持之以恒。戏曲里的练功最是如此,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即便是再恶劣的天气也不可以间断。戏谚常讲:“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功,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功,观众知道。”“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好一张嘴。”除去早晨的喊嗓子,回到京剧院用很短的时间吃过早饭,上午紧接着就是基本功,等饭食消化完后,再练毯子功、把子功、身段课、唱腔课,下午学习文化课,晚上还有晚自习,到了十点准时睡觉。几年如一日,从来没有中断过。
刚开始练功的时候是最令人头疼的。唱戏对腰功、腿功的要求非常高,需要扳腿、压腿、撕腿、杠腰。所
以这行十分看重幼功,因为年龄小时骨骼尚软,等到大时,胳膊腿硬了,再练就不容易了。当时我们的平均年龄都在十四五岁,有大一些的孩子,硬生生地撕腿,其痛苦可想而知。所以每到练功时,偶有从京剧院路过的人听到功房里鬼哭狼嚎的,都以为宰孩子呢。
好在我自恃幼功在身,拿顶、撕腿、下腰什么的我倒是不怕,只是我们在京剧院不管有什么小病小灾,老
师们全都是靠练功给我们“治病”。
有一回我早晨起来肚子疼得厉害,汗珠像黄豆似的,唰唰地往下直滚,实在是练不了功了,就去找老师请假。谁知老师看了看我,用手把我头上的汗珠擦干净,说了一句:“嗯,我知道了,拿大顶去吧。”我一听,心里那股委屈劲就上来了,对老师说:“老师,我不是装的,还得练功啊?”“宝贝儿,少跟我这瞎对付,赶紧练功去!”没有办法,我只得按照老师说的做,找了个墙根,一个倒立把双腿搭在墙上。老师还拿着竹棍,戳着我的腰眼说:“挑腰、立腰、抬头,别懈怠。”我实在憋不住了,心里的委屈全都爆发出来,鼻子一酸,眼泪和着 汗珠滴滴答答地往下直掉,心里甭提多恨这个老师了。老师还是看着我们练功,其他的同学踢腿、溜虎跳、砸毽子。等过了半个多小时,老师用竹棍一指我:“马德华,下来翻几个小翻。”我不情愿地走过去,老师用手抄住我的后腰,我双手一按地,紧跟 着几个后手翻,翻完之后,老师一扶我腰:“活动活动,看看肚子还疼 吗?”我来回抻了抻腰,肚子还真不疼了。
老师瞅了我一眼:“宝贝儿,还肚子疼?身上零件长得倒是挺全的!”当然,练功的时候还是应当以人为本,这种体罚和不负责任的做法现在看来是不可取的。但是,当时老师都是本着严师出高徒、不打不成器的老教条要求我们,实际上也是为了我们有出息,未来成角儿!
严师虽严,但是从心里还是爱护、呵护着我们的。直至现在,我已七十多岁了,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还总爱贴着墙根拿几把大顶,以缓疲劳。皆因老师当年那句:“拿顶,专治肚子疼。”慈母隐泪我在中国京剧院学戏时,只有每周六晚上才能回家,等到周日下午又得回到京剧院。所以,这一天与家人团聚的时间非常珍贵。
我每次回家,都要把换下来的脏衣服带回去给母亲洗。倒不是因为我懒,实在是学戏太辛苦了。老师给我们看功的时候常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当初我们学戏,晚上连炕都上不去。”此话不假,我们每天高强度的训练,到了晚上浑身肌肉酸痛,像是给骨头缝里打了一针浓醋一样。下铺的同学回去倒头便睡,上铺的同学蹬梯上床都费劲,有时候干脆直接扯下褥子,在地上打一宿地铺。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有多余的劲儿去洗衣服啊。
除了洗衣服,每周六我还有一件少不了的功课就是洗澡。母亲知道我学戏苦,每次我一到家,就烧上一盆子热水,好让我洗个澡解解乏。 有一回我刚把衣服脱了,准备进盆,母亲便面色沉重地盯着我的腿上看,说道:“德华,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你腿上是怎么回事?”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发现膝盖周围全都是小紫点,赶紧解释道:“妈,我没打架,没事,不碍事的。
”“不对,这一准是人掐的,你老实说,到底怎么回事?”母亲严厉地问道。
我见实在瞒不过了,便和母亲说了实情。
原来,过去总是讲究打戏,新中国成立之后,剧院里不许再打孩子了,但是相应的教学方法还是要有的。
比如在翻翻的时候,正确的姿势是两条腿必须要直,就好像大车轮一样,翻得飞快才规范、见功夫。 但是刚开始学时,双腿会不由自主地“挂龙”,所谓“挂龙”就是双腿打钩弯曲,这样一来很容易站不稳,速度也减慢了。
老师为了改正我们这个毛病,就想出一个主意,在你翻跟头的时候拿一个竹棍,当你的俩腿一打钩,竹棍就上来敲敲你的腿,跟你强调一 遍别挂龙。可翻跟头是下意识的动作,注意力根本没法集中在腿上,一 连三次挂龙,就不用竹棍了,稍不注意,就用指甲盖掐在腿上,就这么一下子,跟火蝎子蜇了一样,钻心似
的疼。再看这两条腿,跟条件反射一样,登时就直了。等再翻的时候,知道自己哪个地方疼,就知道注意了,到下回保证不带出错的,特别管事。而且这招是只伤皮肉,不伤筋骨,就疼当时一下,过后就好了,对身体也没害处。
我把来龙去脉给我母亲解释完了,就见母亲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里跟我嘀咕:“当时你爸不让你学戏,你偏不听,这回知道苦了吧?”苦是真的苦,但我仿佛真的是乐在其中,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才能站在梦想中的舞台上演戏。所以我坚定地和母亲说:“妈,我不怕苦。”母亲用手背抹了抹眼泪,抱着我换下来的衣服,转身出了门。
多年以后,姐姐和我说,当年母亲最怕每周看我洗澡时遍布腿上的小紫点,所谓“打在儿身,痛在母心”。
我不在家的时候,母亲还偷偷地掉了好几回眼泪。现在回想起母亲,更加体会到慈母那份深沉而又伟 大的爱。
心中打起退堂鼓学戏的日子很苦,但是我也很享受,心中总是有一股子劲儿使我坚持着。一是戏曲这方舞台太有魅力了,它像是一个奇妙的魔术袋子,时时刻刻都有新鲜的东西吸引着我,不知道下一秒又会有什么惊喜;二是我儿时的英雄情结。但是随着对戏曲的深入学习,这种情结从包公、关公、高宠这些戏中的英雄转移到“角儿”的身上了。舞台上精湛的表演,细致入微的刻画,“嘣噔仓”一亮相的碰头好,太光鲜亮丽了。我想着 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什么时候才能穿上蟒袍、扎上大靠,站在舞台中央去演绎我儿时崇拜的英雄啊!
记得电影《霸王别姬》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个学戏的小孩叫小赖子,因为受不了戏班的责打,偷偷跑出戏班,进戏院看了一场《霸王别姬》,当楚霸王项羽出场一亮相的时候,戏园子里像炸开了锅,众人为之倾倒、喝彩,简直要把戏园子掀了顶。小赖子激动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说了句:“这得挨多少打啊!”这段情节很真实,只不过我与小赖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当时我们已经不兴体罚了。“角儿”的光芒一直激励着
我,即使再苦再难,我咬着牙也要坚持下来。
可是有那么一次,我是真的打起了退堂鼓,不想学戏了。
事情的起因是中国京剧院要和北方昆曲剧院合并。因为北方昆曲剧院是1958年刚刚正式建院的,虽然有韩世昌、侯永奎、白云生等大师坐镇,但是青年一代演员相对比较缺乏,所以京剧院决定把一批青年学员调到北昆学习昆曲,其中就包括我。我当时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像揣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那时候的我可是一心只想着演京剧啊! 我实在是太迷京剧了,对昆曲是一窍不通。在我心里,进了京剧院就像是走进了天堂一样美好的地方,现在却突然一下把我打到了一个我极不愿去的地方。而且,我崇拜的英雄偶像都是京剧里的角儿啊!对于昆曲里水磨婉转的曲调,我觉得还是不如一段西皮流水来得痛快。 这种失落的感
觉,除了我,怕是没人能够体会。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把我调到北昆。
那个时候我真是沮丧到了极点,也没了当初学戏时的那股子心劲儿了。借着周末,我回到了家里,父亲要
忙活店里的生意,没在家,只有母亲坐在床上给我姐姐缝补衣服。我凑到母亲身边,说:“妈,我不想学戏了。”母亲愣了一下,放下手中的衣服,盯着我说:“是不是学校的老师、 师兄弟打你了?”我急忙摆手说不是,便将京剧院要把我调去学昆曲这件事一五一十 地跟母亲说了一遍。
母亲瞅了瞅我,叹了口气:“德华,你不是跟你爸爸约法三章,要 干这个,就一定要干到底吗?再说了,即便你回来,再上几年级啊?行了,反正都是唱戏,就别瞎琢磨了。”我没想到母亲会说出这样一句话,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支支吾吾地半天说不出话来。母亲也不看我,接着给姐姐的衣服缝了几针,对我说:“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吧。”那天晚上,我们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饭。父亲看到我回来十分高兴,叫母亲多添了几道菜。哥哥、姐姐对我也是嘘寒问暖,非常关心。我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行为极其不自然。母亲还是照样忙里忙外的,没有多说什么,直到后来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亲。这也算是我和母亲的一个共同的秘密吧!
回到学校,我就去找老师,想继续留在京剧院。老师跟我说,这次被调走的同学都是北方昆曲剧院选的,只有好样儿的才能过去呢。而且这次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京剧界的好角儿,像梅兰芳、杨小楼、谭鑫培等等,都是昆曲戏开的蒙。这样才能做到“六场通透,文武昆乱不挡”,你要是昆曲都能拿得下来,以后就没有能难住你的戏。像武生戏里的《石秀探庄》《挑滑车》《林冲夜奔》,不也得有昆曲的底子吗?
听老师这样一说,我心里才得到了些宽慰。我的梦想不也是要成角儿吗?既然角儿们都学过昆曲,我也不能落下这门功课!此外,我的师兄弟们也全都劝我说:“反正都是一个党委,吃住练功都在一起。空闲的时候吊吊嗓子,以后还能回京剧院。”有了这些鼓励,我的心里才又找回了那股劲儿。(后来还真有一段时间,每逢周日,我就去京剧院和师兄弟们聚在一起练功、谈戏、侃大山。)我原先因为没有接触过昆曲,所以才对它有排斥的心理,可等我真的来到了昆曲剧院,通过不断地学习和了解,我才深深地被这门艺术折服。昆曲实在太高深了,在舞台上讲究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一 招一式都十分讲究。我在这里学的第一出戏是《双下山》,就是我们常讲的“男怕《夜奔》,女怕《思凡》”中的《思凡》。后来这出戏还给两院的党委汇报演出过,反响特别好。我在这出戏里也出了不少彩,给党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出戏甚至还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和人生 轨迹,这些都是后话。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演出,使我更有信心把昆曲学好了。
我被逼上了“梁山”我在前面多次提到我的英雄情结,试问哪个刚演戏的孩子不想站在舞台中央演自己心中的大英雄呢?可是,英雄毕竟是凤毛麟角,这个世界上还是平凡的小人物居多,如果能够把这些小人物演好,不是更加贴近生活,更有意义吗?真正让我想明白这点的,是北方昆曲院决定排练《逼上梁山》,这出戏也着实是把我自己逼上了“梁山”。
我到了北昆之后,最心仪的行当是武生。 但由于我从小调皮,喜欢逗趣,老师一看我这个滑稽劲儿,觉得我更适合唱小花脸,也就是“生 旦净丑”中的丑角儿。我当然不高兴啊,心里总是憋了一口气,心想我凭什么不能当主角?所以,练功的时候,圆场、走边、趟马、起霸,我全都是按照武生的路子去练。我就是想证明自己,我也能成为一个大英雄。
因为北昆当时的青年演员比较少,所以为了培养新人,剧院决定多排几出新戏。我参与的第一出大戏,便是《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这出戏是在延安平剧改革运动中形成的,具有很强的政治品格,昆曲剧院就是按照这个原本改成昆曲的。主角林冲是著名昆曲艺术家、尚派(尚和玉)的传人侯永奎先生。导演是中国第一代戏曲导演,也是当时大咖级的人物—李紫贵老师。由于我在《双下山》中的出色表演,当时党委破格决定让我演高衙内的一个狗腿子—福安。 虽然戏份不是很重,但有几场很讨巧的戏,是调节全剧气氛的一个人物。
那个时候我16岁,正是心气儿高的时候,得知这个消息后并不太高兴,甚至还有一些抵触情绪—凭什么我只能演一个狗腿子?哪怕是让我演李小二也好啊!我堵着一口气,排练也不是很积极。
教我昆丑的一个先生看出我心里不大乐意,有一天突然把我叫到跟 前,对我说:“马德华,你觉得我是个坏人吗?”我一听可吓坏了,不敢说话,只是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这位先生虽然平常教戏时对我们严厉,但是功外对我们特别照顾。
先生接茬说:“戏里面的人物,我演得丑吗?”我不明白先生是什么意思,细细回想了一下先生在舞台上的演出,其实每一个人物都非常诙谐可爱。我还是不敢多说话,只说了两个字:不丑。
先生看了看我,对我说:“德华,这戏台和世界一样,没那么多英雄好汉,要都是英雄好汉,那咱都别过安生日子了。咱虽然是演丑的,可咱这个丑可不是‘丑陋’的意思,是诙谐可爱。唐明皇李隆基,咱们皇上祖师爷就是演丑的。旧社会戏班子后台,咱要不勾脸,没有一个人敢动笔的。那大衣箱二衣箱,除了咱没人敢坐。梨园行里有一句话叫“天下无丑不成戏”,你说咱这个角色重不重要?”我听完这一番话,心里真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原来丑角这么重要 啊!我频频地点头,听着先生的教诲。
“我和你说这些可不是让你搞旧戏班那一套,过去马连良、梅士、 李万春这些艺术家腕儿大不大?虽然被别人当成下九流,可临了妨碍着 人家成角儿了吗?甭管你演什么,首先你得自己瞧得起你自己,对得起你演的人物,不能把他演脏喽!”先生的这一番话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从那往后,我像变了一个人似 的,认真排练,琢磨福安这个人物,想着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小人物演出好来。功夫不亏人,在正式演出的时候,我虽然戏份不多,但是每个包袱都抖响了。看着台下的观众为我演的角色哄堂大笑,我真正体会到“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句话。
导演李紫贵老师还点名表扬了我,说这孩子的感觉太好了,将来一定有出息。
从此,我便走上了学习昆丑的这条路。我相信在舞台上,不管角色大小,只要用心去体验,和所演的角色交朋友,就一定能拿下“好”来。
丑角不丑“文革”是新中国的一场浩劫。但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大抵有两种:一种人愤世嫉俗,浑身充满戾气,正如一坛酒的保存方法不当,会成为一坛子醋;另一种人已经学会苦中作乐。我总想起父亲常说的那句话—自那以后,没有什么值得害怕和抱怨的了。
我更像是后者,在学习昆丑和接受了小人物后,我对待事物的态度已经开始平和了起来。这是一个奇妙的转变—这个世界上需要英雄和救世主,但是相对于悲壮的英雄情结,我更趋向于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我不感谢那个年代,但是纵观我的人生,我感谢它给了我咸涩的滋味。
“文革”开始后,北方昆曲剧院就解散了,停止了一切演出。我又回到了京剧团。有了在北昆打下的昆曲的底子,加上我学戏态度上的改变,我便开始自觉地琢磨、研究小人物。我当时的想法是:袁世海、周和桐、马长礼这些先生的角儿够大吧?不也演反派吗?照样不耽误人家成为艺术家啊!能把鸠山的凶狠残暴、胡传魁的江湖草莽、刁德一的阴险狡诈演得那么生动形象、深入人心,这不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吗?而且样板戏对我的一个很大的提高是,它打破了行当的界限,塑造每一个角色都是从人物出发。例如按照传统戏的路子,刁德一一定就是小花脸,而样板戏却用老生这个行当。这样唱人物、演人物,为我以后拍电视剧积累了不少经验。
所以,我便踏踏实实地演戏,认真塑造每一个角色。我演了不少样板戏中的反派角色,比如《海港》里的钱守围、《审椅子》里的王老虎、
《沙家浜》里的刁德一等。有了这些磨炼和舞台经验的积累,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先生说的那句话—丑角不丑。
戏曲与影视的区别寒冬再长,春天总会到的,冰冷的东西开始融化,万物开始复苏,一切都是朝气蓬勃的景象。那个时候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说不完的话,想要一股脑地倒出来。我们开始演样板戏以外的戏了,我一下子仿佛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里,眼界的开阔使我不由自主地汲取外界的营养。 我拍摄了我的第一部戏曲电影《血溅美人图》,在里面出演吴三桂这个人物。
《血溅美人图》的导演是沙丹先生。我当时还从未涉足影视,所有的表演还都局限在戏曲舞台上的经验。
舞台上的演出是夸张的艺术,不信各位看戏曲中的花脸,实则是把人物的特点放大,给观众以更强的冲击力。但是放到荧屏上又是另外一码事了,影视有单独的一套镜头语言,它可以随意切换角度,达到放大人物情感的效果。我因此闹了不少的笑话,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三报”这一场戏。
“三报”是李自成大兵压境,吴三桂派人护送陈圆圆入山海关,自己稳坐在中军大帐听探马蓝旗官来禀报刺探来的消息。头一报是“陈圆圆已经启程入关”,第二报是“陈圆圆被山贼掳走”,第三报是“陈圆圆被李自成抢走”,这才促使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当我听到第一报的时候,人物内心是喜悦和兴奋的,脸上的表情应当是高兴,我按照舞台上的经验把戏做足了。不料这个时候导演喊了声“咔”。我脑子一蒙,我这点没毛病啊?我就问导演:“导演,我这点戏怎么了?”导演就说了一句话:“收着点。”我不明所以,我这点戏多好啊,为什么要收着?等到听到第二报“陈圆圆被山贼掳走”时,我把眉头紧锁
,眼睛瞪大,脸部的肌肉全都绷紧起来,鼓足丹田气喊了一声:“啊,再探再报!”导演这次有点火了:“马德华,你这是第几报?”我说:“第二报啊。”导演说:“那你第三报怎么办?”我听导演这么一说,彻底不会演了。这要是在剧场里演,“三报”下来是要起尖的(观众是要喊好的)。
我说:“导演,我怎么囤的我怎么卖,当初学戏的时候先生就是这么教的,我不知道毛病在哪儿啊!”导
演跟我说:“舞台上的表演和影视里面的不一样。在剧场里,那么多观众看你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你夸张一些恰到好处。但这是电影,这场戏是要用推镜头给你一个面部特写的,本来推镜头就会增加人物的情感,再来一个面部特写,整个荧屏上就你的一张脸,你的表情又这么狰狞,还不把观众吓着?这戏就没法看了,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哦!”我一拍脑门,恍然大悟,好像找到些诀窍,当时就说:“导 演,咱再来一遍。”这回我一边演戏,一边看着镜头。等镜头向我推过来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劲头、分寸全都收着使。等镜头拉远了,我再适当地把戏做足。
这“三报”全部拍完了,导演一喊“咔”,冲我嚷了一句:“嘿,马德华,你小子还真灵!”俗话说:“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正是这次闹的笑话,让我知道了戏曲以外的表演方法和技巧,为我接下来的人生转折点—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不能把角色演脏了很多事说来也巧,1982年的时候,北昆决定排《孙悟空大闹芭蕉洞》,组织上决定让我演猪八戒。虽然猪八戒是一个很讨巧的人物,但我不想把他演成只会出丑、搞笑、无厘头的人物。我观摩了很多前辈老先生
的演出资料,做足了功课。
此外,我的恩师郝鸣超先生还给我讲了几则梨园行的逸事。
在旧社会演戏,很多演员为了博观众一笑,或者为了演出时效果火爆,故意在台上出一些洋相,耍一些滑稽,其实根本不符合人物的身份。 但真正的前辈艺术家们绝不会脱离开人物去演戏。京剧界有一个前辈叫杨小楼,是公认的武生泰斗,他演戏的时候从来不追求戏外的好,但是观众看完戏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细细一咂摸滋味,这角儿真好!这个好才是值钱的好。
第二则逸事,京剧谭派的创立者谭鑫培谭老板,有一天和朋友去看当时梨园界很红的演员演的《洪洋洞》。这出戏讲的是杨六郎身染重病,又得知二位兄弟孟良、焦赞为盗老令公的尸骸而命丧北国番邦,气绝身亡的故事,所以又叫《三星归位》。这位演员饰演杨六郎,他临上场时得知谭鑫培来看戏,便铆足了劲地唱。其间谭鑫培一语不发,到戏的最 后和朋友说了一句:咱看他怎么死。
另外还有一则逸事。武生名家厉慧良先生在京剧《长坂坡》中饰演主角赵云,其中“抓帔”一折真的是演神了。当糜夫人要投井时,厉慧良饰演的赵云向前要抓住糜夫人,却把糜夫人的帔抓了下来,匆忙中往 空中一抛,接着走返绷子,等帔从空中落下时,在锣声一击中接在手中,亮相,台下准是满堂彩!
在《长坂坡》这出戏里,刘备本是二路老生,用现在话说就是配角。 一般演出时,主演为了凸显自己,经常是赵云上场,卖弄一番本领后,四击头亮相。可厉慧良饰演赵云时,却先让刘备四击头亮相,自己则是简单地亮相。
有人问厉慧良:“您的赵云出场怎么给刘备这么多戏?”厉慧良说:“首先,刘备是主公,赵云不能盖过刘备。其次,赵云也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我演的是人物,不是角儿!”所以,先生的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刻—戏里的人物不能演脏喽。 人物要有性格、有血肉,要能够给观众咀
嚼和回味,才能得到观众真正的叫好。
看戏是我最大的乐趣我要感谢那段尚无为的岁月,就像苏东坡所说的一样: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虽然我从事戏曲工作这条路似有不顺,有两三次不遂人愿,但现在看来,这些无疑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我爱戏,是从骨子里热爱。举个例子,我初到北京京剧院时,功房里的锣鼓声震人耳膜,我却能在文武场边上睡着了,仿佛这是世间最美妙动听的音乐,把我受过的委屈、吃过的苦全都消融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剧团在宣武门,长安大剧院在西单。所有进京的各个剧种都要到长安大剧院演出,我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每天都约上三五个师兄弟去看戏。有一次是浙江宁波的甬剧《半把剪刀》来京演出,我叫了几个同学一起去,他们一听是甬剧,便说:“甬剧你听得懂吗?”我说:“听不懂咱们坐在那儿看看热闹呗。”到了剧场,因为有语言上的障碍,这戏是真的听不懂。我这人就有这么点长处—适应性强,能压着自己看,而且还看了好几遍,慢慢还真能品出来一些滋味,看出来人家的好了。
还有高甲戏,只有高甲戏是以小花脸为主角。《连升三级》中的张好古、《僧尼会》中的小和尚,有很多小花脸的技巧和京剧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我都能接受。
后来去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农村教育的时候,我就能够演湖南的花鼓戏、山东的莱芜梆子、江西的采茶戏,观众特别欢迎。甚至我总在长安大剧院听侯宝林先生等一些大师的相声,也能化在自己的身上,后来联欢会的时候还和程之老师、韩善续老师一起表演过相声节目。
后来,我在饰演猪八戒的时候,还能想起来某些动作是得益于我看的哪出戏。那时我才真正明白,演员就应该像海绵一样,不断地从外界汲取养分,这些艺术上的直观感受是潜移默化的。苏东坡说过:“博观 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此话当真不假,细细想来我也是从这博观和厚积中成长的。
这个八戒,通日语,擅芭蕾,精书法,唱戏更是老本行……他从不要求做男一号,但永远用男一号的标准塑造男二号!
他把日子过成段子,他是八戒,又不止八戒!
六小龄童、迟重瑞、汪粤、刘大刚等众多明星联袂推荐!
亲,大宗购物请点击企业用户渠道>小苏的服务会更贴心!
亲,很抱歉,您购买的宝贝销售异常火爆让小苏措手不及,请稍后再试~
非常抱歉,您前期未参加预订活动,
无法支付尾款哦!
抱歉,您暂无任性付资格